前一頁
回目錄
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9] 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的一個抗日故事。這种民間立場首先体現在作品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形象這兩個方面。對于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并不少見,但《紅高粱》与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虛擬家族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余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這部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主干寫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的起因和過程;后者由余占鰲与戴鳳蓮在抗戰前的愛情故事串起。余占鰲在戴鳳蓮出嫁時做轎夫,一路上試圖与她調情,并率眾殺了一個想劫花轎的土匪,隨后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里野合,兩個人由此開始了激情迷蕩的歡愛,接下來余占鰲殺死戴鳳蓮的麻瘋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我們不難看出在這條故事線索中,始終被突現出來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間激情,它包容了對性愛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為其根本。這顯然逾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對民間世界給予一种直接的觀照与自由的表達。前一條抗日的故事線索,從戴鳳蓮家的長工羅漢大爺被日本人命令殘酷剝皮而死開始,到余占鰲憤而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隊,于是發動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參加的民間戰爭。整個戰斗過程体現出一种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欲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种自然主義式的生存斗爭。概括的說,《紅高粱》在情節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間自身的主題模式,盡管它講述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主要都是民間世界中強憾生動的暴力与性愛內容。与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傳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為“我爺爺”出場的余占鰲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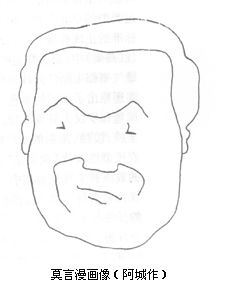 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50-70 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准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但在《紅高粱》中,余占鰲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气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准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這些特點也同樣体現在對于“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溫熱、丰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忍、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沖動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間的放縱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体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的表達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間价值尺度認同的傾向。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狀態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馴的個性与行為,才能那樣自然的創造出一种強勁与質朴的美。
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50-70 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准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但在《紅高粱》中,余占鰲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气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准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這些特點也同樣体現在對于“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溫熱、丰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忍、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沖動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間的放縱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体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的表達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間价值尺度認同的傾向。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狀態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馴的個性与行為,才能那樣自然的創造出一种強勁与質朴的美。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并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里的有所寄托。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歎,极力贊美他的故鄉,贊美他的那些豪气蓋天的先輩,并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這种感歎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愈加變得濃烈感人,其中所体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間作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机昂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敘述者以這樣一种民間的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种狀態只是過去時態的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進步隱含种性退化的感慨。這里顯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傳統都全然無關的歷史評判尺度: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歷史發展与社會現實境況,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狀態受到限制的趨向。而在《紅高粱》中,這种遺憾与感慨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曾經存在過的民間自在狀態的理想化与贊美,從而使其呈現出了更為燦爛奪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間世界認同為一种理想狀態,事實上也會使描繪其中粗鄙丑惡的一面變得自然起來:像《紅高粱》中有關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畫,有關殘酷殺戮(特別是剝人皮那個自然主義式的血腥場面)的描寫,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諧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种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与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种傾向在《紅高梁》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怀。但就新歷史小說后來的走向而言,由《紅高粱》開拓的這种對民間粗鄙形態不加選擇的表現方式,愈加顯現出低俗趣味的性質,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間理想的支撐,這類描寫就很自然地墮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縱,而喪失了向民間認同所應具有的人文意義。
有關《紅高粱》,值得述及的還有這部小說在寫作上的新穎之處。莫言曾較深地受到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從他們那里大膽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時空表現手法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結构方式,他在《紅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与情節邏輯,把整個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這种看來任意的講述卻是統領在作家的主体情緒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這部小說中還顯示出了駕馭漢語言的卓越才能,他運用了大量充滿了想象力并且總是違背常規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辭手法,在語言的層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麗神奇的特點,以此造就出了整個小說中那种异于尋常的民間之美的感性依托。
注釋:
[1] “新寫實”現象最早是1988年秋在無錫由《文學評論》雜志和《鐘山》雜志聯合舉行的“現實主義与先鋒派”研討會上提出來加以討論的。起先有多种提法,如“后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等等,《鐘山》雜志1989年第3 期上開辟“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正式确定了“新寫實主義”的名稱。
[2] 所有這些作家對這一命名方式几乎都持否認或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并且他們的創作風格也各有相异之處,很難將其全都划入到一個絕對統一的理論概括之中;這都說明所謂新寫實小說只能算是一定時期內的一种創作傾向,而不是一种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
[3] 參閱張業松《新寫實:回到文學自身》,收入《個人情境》,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年版,32頁。
[4] 引自陳思和:《關于“新歷史小說”》,收入《雞鳴風雨》,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5] 《風景》,初刊于《當代作家》1987年第5 期。
[6] 《一地雞毛》,初刊于《小說家》1991年第1 期。
[7] 引自劉震云《磨損与喪失》,《中篇小說選汞》1991年第2期。
[8] 引自陳思和等對話《劉震云:當代小說中的諷刺精神到底能堅持多久?》,收入《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頁。
[9] 《紅高梁》初刊于《人民文學》1986年第3 期,莫言后來把《紅高粱》及其續篇《高粱酒》、《狗道》、《高粱殯》、《狗皮》這五部中篇小說合成為了一部情節連貫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文討論的仍是最初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梁》。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